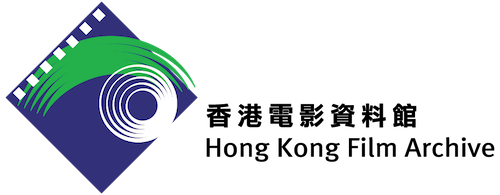粵港電影因緣
前言
去年底看周星馳的《功夫》(2004),當元秋推開房窗伸出頭來,牙刷插在泡着牙膏沫的咀角邊,大聲咆哮着:「樓下邊鬼個閂咗水喉呀?」心裏不禁暗叫一聲。元秋演的「小龍女」,活脫脫就是《七十二家房客》裏譚玉真演的包租婆,忍不住套用麥兜波蘿油王子小女友的一句讚嘆語:勁呀!這裏說的不是楚原於1973年為邵氏執導的那一部,而是王為一於1963年為廣州珠江電影製片廠編導的原裝版。《七十二家房客》本是上海的一齣滑稽劇,被移形換影搬去了廣州,在六十年代香港左派公司的資金和社會主義紅旗下的片廠裏,重塑羊城四十年代的舊時風貌。七十年代,同一個故事又在香港邵氏影城裏再次包裝,令粵語片起死回生。三十餘年後,周星馳挾着美國資金跑到上海去拍《功夫》,在昔日十里洋場之地搭建起豬籠城寨來。當馮小剛飾演的黑幫大佬發現自己身陷絕境時,敵對的斧頭幫說:「當你喺度打警察的時候,你的馬仔全都去學廣東話了。」典型的星爺式黑色幽默,倒令人想起早年香港電影的面貌來。
二十及三十年代之初,我們只有國產片,沒有「港產片」,但自從薛覺先為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拍了中國第一部粵語片《白金龍》(1932)後,親切的「哩、啦、哦、噃」之粵聲就透過菲林響徹港澳、兩廣、東南亞、甚至美洲等地,幾乎沒有間斷過,就連三十年代中期擾攘一時的禁粵語電影運動,最終也只能不了了之。當年有報道稱阮玲玉曾離開「聯華」加入「天一」,並會主演一部慕維通聲片(廣州《伶星》,第31期,1932年4月13日)。這一段娛樂新聞不知是真是假,但阮玲玉一直沒有離開聯華;要不然,我們就可能會聽到她開腔了;她是廣東人,「天一」很可能乘勢追擊讓她拍粵語片吧。若留意看看三十年代有聲電影發展初期的電影廣告,常會見到強調「廣東人」或「粵影界」的廣告,倒鮮見「香港」這面招牌,可見當時粵港兩地的關係極為密切,在民間交往的層面上幾乎無分彼此,而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口邊的「香港認同身份」還未真正建立起來。
就粵港兩地在電影方面的交流,周承人的〈粵、港影界互動〉作了簡潔握要的闡述。李培德、鍾寶賢及韓燕麗則從上海與香港、國語與粵語、國族大義與語言統一等政治、經濟、文化關係,去探討早期粵語電影的生存空間。幾乎每個作者都有提及三十年代中期的禁粵語電影運動,事實上,這場運動背後的各種矛盾也真的是千絲萬縷,糾纏不清。早期活躍於中國影壇的影人,不少都來自廣東,其中黎民偉、黎北海兄弟對中國和香港影業都貢獻良多。前者早已有不少電影史學者作出研究,我們趁這次機會訪問了他的後人,他們談黎氏的教育和社交圈子,對研究者應饒有趣味;至於黎北海,李以莊則從省港大罷工後香港電影重建的角度來肯定他的地位,可說是填補了香港電影史上的一個缺位。跟黎氏兄弟一樣,羅明佑也是廣東人。他生於香港,其電影事業始於北京,盛於上海;但他和黎氏兄弟創辦的「聯華」,卻在很大程度上建基於他們深厚的粵港社會關係,而他最終亦返回出生地的香港。傅葆石嘗試重塑羅明佑的電影人生,周承人則細析「聯華」的結構,將香港、廣州和上海同時放在中國電影史的大版圖上來審視。
香港位於廣東南端,粵港本來就是一家,即使在殖民地的管治下,香港早年普通民眾的生活習慣、風俗人情,還是跟廣東非常相近。翻看二、三十年代的香港報章,篇幅上粵省新聞常比本港新聞佔更大的比重,老倌領着粵劇班穿梭往來粵港澳的廣告也非常熱鬧。粵劇對香港電影的影響深遠,從題材、類型到幕前幕後的人材,都處處見其影子。當年薛(覺先)馬(師曾)爭雄,從舞台爭到銀幕,從廣州爭到香港,其後兩位都於1949年後返回中國。薛覺先留下來的電影很少,難於討論,馬師曾倒在菲林上留下了不少可供賞析的痕跡。看《審死官》(1948),百份百肯定周星馳向他隔世偷師;看《賊王子巧遇情僧》(又名《糊塗外父》,1952),笑得全組同事人翻馬仰,他和劉克宣分演老夫老妻,後者反串演出,真虧他們抵死若此,大概只有丑生出身的他們那一輩,才可以這麼有戲味。古蒼梧撰文分析馬師曾如何以他的舞台藝術豐富了香港的電影。羅卡則對任護花情有獨鍾。任在三十年代是廣州的記者、流行作家、開戲師爺,其後來港,辦小報、寫流行小說和影評、拍電影,身兼多職,是香港特產的跨界奇人。天空小說家李我,生於廣州,在香港受教育,戰時生活顛沛流離,戰後以其天空小說瘋魔粵港澳,他本人的故事就是一部最曲折奇情的小說。資料館的同事為他做口述歷史訪問,就如聽了一場精彩的真人show。黎肖嫻一邊看從他的小說改編過來的電影,一面對照着他的訪問,構成了非常有趣的閱讀。而王為一,從上海南來香港,在左翼影人蔡楚生的支持下拍了《珠江淚》(1950),為香港電影留下了一部經典之作;其後他返回國內,參與珠江電影製片廠的建立,是南國電影的關鍵人物之一。朱順慈專程去廣州訪問老人家,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一手資料,彌補我們缺失了的記憶。
記憶這回事,有點像水,放進甚麼容器裏就是甚麼形狀。我們的廣州印象,在四十年代,是當下;在五十年代,是剛過去;踏入六十年代,已是有點模糊;再往後,大抵就要多加幾分想像了。廣州這座城市如是,廣東傳奇也如是。三、四十年代廣州天台遊樂場裏的《桃花江》裏的美人與英姿颯颯的《穆桂英》毗鄰而居,相安無事;陳夢吉輪迴轉世,從廣東市井的民間潛入了現代香港人的集體意識裏,近年更穿上了「無厘頭」的時裝,在神州大地上狂野奔馳;黃飛鴻開始時帶點流氓習氣,很快就板起了師道尊嚴的面孔,七十年代後回復青春,近年更企圖國際化。幾位影痴朋友藍天雲、何思穎、蒲鋒等帶隊進入電影的虛幻世界,掏找一些我們早已遺忘了的東西。香港身處中國之南,屬嶺南地區,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列孚斬釘截鐵地說:我們的電影與嶺南文化零距離!這是一個富爭論性的提法,相信會引起各家爭鳴。程美寶的文章主要探討的不是電影,而是語言,似乎埋錯了堆,但香港電影的在中國電影史上佔了那麼獨特的一個位置,正正在於其語言文化的邊緣、多變與開放。
以前討論香港電影,往往只談上海對我們的影響,卻原來近在眼前的廣州淵源最深,多虧羅卡想出了「珠三角:電影.文化.生活」這個放映專題。余慕雲先生去年為資料館搜集早期影人的資料,為此次專題研究奠下了基礎。前輩影人的經驗之談,對研究者來說是最寶貴的資料。編者沒有史學的訓練,跟幾位歷史學者討論問題時獲益良多,更難得他們在百忙中為本書撰稿。志趣相投的朋友們一起看電影談電影寫電影,永遠樂趣無窮。當然,最感激身邊的一班同事,全職的、兼職的,他們熱誠認真,常常看到我看不到的問題。謝謝你們。
黃愛玲
2005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