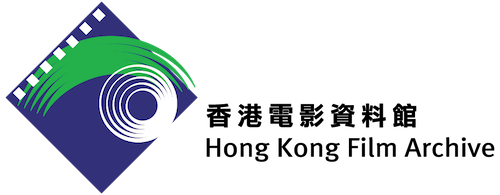粤港电影因缘
前言
去年底看周星驰的《功夫》(2004),当元秋推开房窗伸出头来,牙刷插在泡着牙膏沫的咀角边,大声咆哮着:「楼下边鬼个闩咗水喉呀?」心里不禁暗叫一声。元秋演的「小龙女」,活脱脱就是《七十二家房客》里谭玉真演的包租婆,忍不住套用麦兜波萝油王子小女友的一句赞叹语:劲呀!这里说的不是楚原于1973年为邵氏执导的那一部,而是王为一于1963年为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导的原装版。《七十二家房客》本是上海的一出滑稽剧,被移形换影搬去了广州,在六十年代香港左派公司的资金和社会主义红旗下的片厂里,重塑羊城四十年代的旧时风貌。七十年代,同一个故事又在香港邵氏影城里再次包装,令粤语片起死回生。三十余年后,周星驰挟着美国资金跑到上海去拍《功夫》,在昔日十里洋场之地搭建起猪笼城寨来。当冯小刚饰演的黑帮大佬发现自己身陷绝境时,敌对的斧头帮说:「当你喺度打警察的时候,你的马仔全都去学广东话了。」典型的星爷式黑色幽默,倒令人想起早年香港电影的面貌来。
二十及三十年代之初,我们只有国产片,没有「港产片」,但自从薛觉先为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拍了中国第一部粤语片《白金龙》(1932)后,亲切的"哩、啦、哦、噃"之粤声就透过菲林响彻港澳、两广、东南亚、甚至美洲等地,几乎没有间断过,就连三十年代中期扰攘一时的禁粤语电影运动,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当年有报道称阮玲玉曾离开「联华」加入「天一」,并会主演一部慕维通声片(广州《伶星》,第31期,1932年4月13日)。这一段娱乐新闻不知是真是假,但阮玲玉一直没有离开联华;要不然,我们就可能会听到她开腔了;她是广东人,「天一」很可能乘势追击让她拍粤语片吧。若留意看看三十年代有声电影发展初期的电影广告,常会见到强调「广东人」或「粤影界」的广告,倒鲜见「香港」这面招牌,可见当时粤港两地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民间交往的层面上几乎无分彼此,而我们今天常常挂在口边的「香港认同身份」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就粤港两地在电影方面的交流,周承人的〈粤、港影界互动〉作了简洁握要的阐述。李培德、钟宝贤及韩燕丽则从上海与香港、国语与粤语、国族大义与语言统一等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去探讨早期粤语电影的生存空间。几乎每个作者都有提及三十年代中期的禁粤语电影运动,事实上,这场运动背后的各种矛盾也真的是千丝万缕,纠缠不清。早期活跃于中国影坛的影人,不少都来自广东,其中黎民伟、黎北海兄弟对中国和香港影业都贡献良多。前者早已有不少电影史学者作出研究,我们趁这次机会访问了他的后人,他们谈黎氏的教育和社交圈子,对研究者应饶有趣味;至于黎北海,李以庄则从省港大罢工后香港电影重建的角度来肯定他的地位,可说是填补了香港电影史上的一个缺位。跟黎氏兄弟一样,罗明佑也是广东人。他生于香港,其电影事业始于北京,盛于上海;但他和黎氏兄弟创办的「联华」,却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他们深厚的粤港社会关系,而他最终亦返回出生地的香港。傅葆石尝试重塑罗明佑的电影人生,周承人则细析「联华」的结构,将香港、广州和上海同时放在中国电影史的大版图上来审视。
香港位于广东南端,粤港本来就是一家,即使在殖民地的管治下,香港早年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风俗人情,还是跟广东非常相近。翻看二、三十年代的香港报章,篇幅上粤省新闻常比本港新闻占更大的比重,老倌领着粤剧班穿梭往来粤港澳的广告也非常热闹。粤剧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深远,从题材、类型到幕前幕后的人材,都处处见其影子。当年薛(觉先)马(师曾)争雄,从舞台争到银幕,从广州争到香港,其后两位都于1949年后返回中国。薛觉先留下来的电影很少,难于讨论,马师曾倒在菲林上留下了不少可供赏析的痕迹。看《审死官》(1948),百份百肯定周星驰向他隔世偷师;看《贼王子巧遇情僧》(又名《糊涂外父》,1952),笑得全组同事人翻马仰,他和刘克宣分演老夫老妻,后者反串演出,真亏他们抵死若此,大概只有丑生出身的他们那一辈,才可以这么有戏味。古苍梧撰文分析马师曾如何以他的舞台艺术丰富了香港的电影。罗卡则对任护花情有独钟。任在三十年代是广州的记者、流行作家、开戏师爷,其后来港,办小报、写流行小说和影评、拍电影,身兼多职,是香港特产的跨界奇人。天空小说家李我,生于广州,在香港受教育,战时生活颠沛流离,战后以其天空小说疯魔粤港澳,他本人的故事就是一部最曲折奇情的小说。资料馆的同事为他做口述历史访问,就如听了一场精彩的真人show。黎肖娴一边看从他的小说改编过来的电影,一面对照着他的访问,构成了非常有趣的阅读。而王为一,从上海南来香港,在左翼影人蔡楚生的支持下拍了《珠江泪》(1950),为香港电影留下了一部经典之作;其后他返回国内,参与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建立,是南国电影的关键人物之一。朱顺慈专程去广州访问老人家,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弥补我们缺失了的记忆。
记忆这回事,有点像水,放进什么容器里就是什么形状。我们的广州印象,在四十年代,是当下;在五十年代,是刚过去;踏入六十年代,已是有点模糊;再往后,大抵就要多加几分想像了。广州这座城市如是,广东传奇也如是。三、四十年代广州天台游乐场里的《桃花江》里的美人与英姿飒飒的《穆桂英》毗邻而居,相安无事;陈梦吉轮回转世,从广东市井的民间潜入了现代香港人的集体意识里,近年更穿上了「无厘头」的时装,在神州大地上狂野奔驰;黄飞鸿开始时带点流氓习气,很快就板起了师道尊严的面孔,七十年代后回复青春,近年更企图国际化。几位影痴朋友蓝天云、何思颖、蒲锋等带队进入电影的虚幻世界,掏找一些我们早已遗忘了的东西。香港身处中国之南,属岭南地区,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列孚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电影与岭南文化零距离!这是一个富争论性的提法,相信会引起各家争鸣。程美宝的文章主要探讨的不是电影,而是语言,似乎埋错了堆,但香港电影的在中国电影史上占了那么独特的一个位置,正正在于其语言文化的边缘、多变与开放。
以前讨论香港电影,往往只谈上海对我们的影响,却原来近在眼前的广州渊源最深,多亏罗卡想出了「珠三角:电影.文化.生活」这个放映专题。余慕云先生去年为资料馆搜集早期影人的资料,为此次专题研究奠下了基础。前辈影人的经验之谈,对研究者来说是最宝贵的资料。编者没有史学的训练,跟几位历史学者讨论问题时获益良多,更难得他们在百忙中为本书撰稿。志趣相投的朋友们一起看电影谈电影写电影,永远乐趣无穷。当然,最感激身边的一班同事,全职的、兼职的,他们热诚认真,常常看到我看不到的问题。谢谢你们。
黄爱玲
2005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