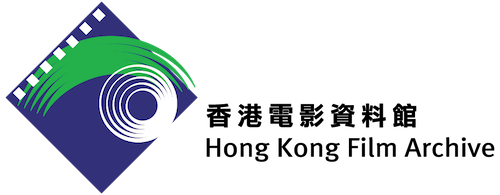冷戰與香港電影
導論
李培德、黃愛玲
冷戰不是新課題,特別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中外研究成果甚多。傳統上,美國對於冷戰研究一直佔著優勢,但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前蘇聯、東歐和國內檔案逐步開放,令冷戰研究日漸國際化,華人學者的參與更變得越來越重要。2006年10月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和香港電影資料館聯合舉辦了「1950至1970年代香港電影的冷戰因素學術研討會」,嘗試從文化、社會角度探索冷戰和本地電影的關係,頗具挑戰性。正如科大衛在主題演講中所說,冷戰可分大冷戰和小冷戰。大冷戰是指美蘇兩國的競爭,也包括意識形態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壘,小冷戰是指國共兩黨在香港的鬥爭。香港過去由於是英屬殖民地,居民以華人為多,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處於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夾縫,華人政治圈內則拉鋸於海峽兩岸政權之間。不過,從此亦可見香港地位的獨特之處。
那麼,在這大小冷戰刀來劍往、暗湧四伏的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是否只擔當了一名荷戟獨徬徨的小卒角色呢?恰恰相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退守台灣,兩地都被鎖進意識形態鬥爭的堡壘裡,倒讓我們這塊小小殖民地找到了特殊的生存空間,孕育了生命力旺盛的香港電影。回溯戰前甚至戰後初期的香港電影,一直都是粵語片的天下,偶爾有三數部國語片,不成氣候。戰後,外敵雖已敗退,國共兩黨卻未能相容,爆發激烈內戰,大量人才和資金從上海南下香港,五十年代星馬資金亦大量流來香港,積極介入香港電影業,造就了粵語和國語電影平衡共存的獨特生態,這種局面竟然維持了二十多年,直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粵語影業全面停產為止。這段時期見證了香港電影發展的重要歷史。
如果說香港電影於八十年代開始蜚聲國際,那麼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又有何特色,如何與八十年代的發展扣上關係呢?在人才培養、市場開拓、資本累積,以至電影類型和風格內容的演變,冷戰時代的香港電影界如何為現在我們所熟悉的港產片創造神話的基石?冷戰對香港電影所產生的影響,或許可用這樣一個淺易的道理來說明:沒有冷戰便沒有邵氏,沒有邵氏便沒有TVB(無線電視),沒有TVB便沒有新浪潮電影,沒有新浪潮電影便沒有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的風光。當然,這樣「沒有下去」是沒有意思的,最重要的是要指出冷戰時代香港電影界所發生的事,而這些事對以後的香港電影所造成的影響。
本書各文章的作者,來自不同背景,有歷史學者、文化社會學者、電影研究者和從電影界退下火線的前輩。由於背景相異,在觀點和方法上自然不會一致。不過,從多元角度去討論冷戰時期的香港電影,也就成為本書的特色。通過本書,讀者或可發現電影分析是可以和歷史研究、文化研究、社會研究相結合。過去有人說,做電影史的人分兩類,一類只看電影,不重視文字檔案,一類只重視可靠的文字紀錄,忽略電影本身。其實,兩種方法之間可以互補不足。坦白說,電影研究與電影史研究無大分別,都須面對怎樣駕馭材料和分析文本的問題。除了方法之外,本書的另一特點在於引用不少第一手原材料,包括政府和私人機構的檔案、口述訪問紀錄等。
本書分六大部分,除第五部分外,各收三篇文章。第一部分是本書討論主題的背景。科大衛的文章從生活去告訴我們冷戰的意義,指出香港的左右派之爭只屬於小冷戰,沒有達到「熱」的程度,強調香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於六十年代都有其時代特色,為本書提供了討論的線索。周承人的文章描繪了從新中國成立前到1966年文革爆發前香港左派電影圈,包括長城、鳳凰、新聯三公司的成立過程,並討論內地和香港政府對之態度,提出了左右派陣營劃分的最主要標準,在於國家認同和政治理念的分別。張濟順的文章把討論中心轉移到上海,指出在冷戰初期上海雖然驅除了西方電影的影響,卻無法禁絕大受基層群眾歡迎的香港電影;這裡指的當然是左派公司如長城、鳳凰的出品。根據作者的分析,香港儼然代替了西方的位置,由於受到上海市民歡迎,使有關當局不僅同意引入香港左派電影,更對香港電影界採取積極的統戰政策。
第二部分是冷戰時期的香港電影工業與政治。吳國坤的文章,主要討論戰後香港電影的審查制度和左派電影如何因應電檢制度而作出適當調整,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左派電影並非如我們所想的只會強調意識形態,不講其他內容。相反,左派電影的內容是多樣性的。同時,香港政府對電影的審查亦非一成不變,時鬆時緊,檢查與被檢查之間好像有一種互動關係。黃仁的文章討論右派電影陣營在香港的發展過程,可謂與前面周承人的文章互相呼應。作者把重點置於電影人和電影機構,指出兩派陣營有過激烈的競爭。在國共鬥爭的前提下,香港影人蒙受了不少損失,不過作者在文章結尾部分補充,香港於冷戰時期的電影對造就八十年代有名的導演有著正面的作用。與黃仁的文章剛相反,李培德提出冷戰時期香港的電影界雖分左右陣營,但之間經常合作,尤以邵氏與長城、鳳凰、新聯三公司的關係最為密切,而影人在兩派之間游走,更非罕見。該文利用有關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的資料,討論1979年香港無線電視演員因赴廣州出演節目,被迫寫悔過書的經過,反映了香港影人處於國共兩黨政權夾縫裡的無奈,這些資料最近由香港電影資料館整理出來。
傳媒乃政治必爭之地,第三部分討論五、六十年代左右兩派如何爭取傳媒陣地,擴大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影響。打從三十年代開始,左翼一直注重發展「進步評論」。戰後,南來的左翼文人影人不但攝製進步電影,同時積極開拓在報紙上的進步評論園地,吳詠恩的文章便勾勒出左翼評論對香港粵語電影的影響。三十年代粵語電影險遭禁絕,戰後以蔡楚生為代表的粵語電影評論,從方言的文化價值出發,對粵語電影加以肯定,使其日後發展成本土色彩濃厚的港產片。羅卡曾任《中國學生周報》編輯,他以過來人的身份縷述《學周》從創刊至停刊22年期間的變化。1952年創刊時,正值韓戰後期,美國對中國大陸實行軍事、政治、經濟與文化圍堵。有明顯美援背景的《學周》在五、六十年代左右派文化統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引進西方現代電影思潮,從而衍生了七十年代香港的新電影文化,值得我們重新回顧。當年同樣接受美援的亞洲出版社,出版旗艦刊物《亞洲畫報》及學術著作、反共小說等書籍。一年後,主持人張國興成立亞洲影業,五年間拍了九部電影。容世誠將亞洲出版社和亞洲影業的出版事業和電影製作,置於同時代的香港歷史處境來分析,並將亞洲影業和電懋聯繫起來,使箇中的脈絡更清晰明朗地浮現出來。
在第四部分裡,作者將視點從大歷史移向個人的小故事。黃愛玲的文章從朱石麟和岳楓的電影人生出發,探討從事創作的人在特定的歷史環境裡如何自處,如何在種種客觀的條件局限中生存下去,並嘗試尋找自己的出路。朱石麟和岳楓二人背景相近,都在三十年代初投入電影界,上海租界淪陷時期皆留滬拍片,戰後南來香港,分別成為了冷戰年代左右兩個電影陣營的骨幹人物。同樣以兩位同年代但又分屬左右陣營的電影導演為個案,朱順慈從口述歷史出發,分析和比較王天林和胡小峰如何敘述他們的冷戰經驗,並初步探討口述歷史在電影研究中的優勢和局限。口述歷史雖然也可說是一種歷史書寫,但敘事者選擇說甚麼內容,以及怎樣說,都隱含了當事人的主觀判斷和評價。如從這角度去閱讀口述歷史,可開拓更多詮釋歷史的可能性。鍾寶賢則獨挑張善琨來述說她的冷戰故事。張善琨在戰後一片「嚴懲漢奸」的呼嘯聲中南來香港,先後參與了永華、長城和新華的創業,並發起右派的自由總會,成為了台、港之間娛樂業和政治圈的橋樑。
第五部分是冷戰時期電影文本的討論。麥欣恩以六十年代電懋與日本東寶公司合作拍攝的「香港」系列作為討論對象,追溯冷戰在亞洲地緣政治及大眾文化所遺留下來的痕跡。「香港」系列共有三部電影,從1961到63年,每年製作一部,分別是《香港之夜》(1961)、《香港之星》(1962)、《香港.東京.夏威夷》(1963)。韓燕麗以倫理親情片為切入點,嘗試管窺主流香港電影由文藝片到歌舞片、武俠片、功夫片的轉變過程,從而探討戰後至六十年代末,香港電影如何在市場和政治的雙重壓力下,陷入政治失語的困局。六十年代,鐵金剛影片席捲全球,冷戰成為間諜歷險動作片的指定主題,香港影壇也出現了有趣的變奏。何思穎的文章分析了粵語片的「珍姐邦」和國語片的「亞洲鐵金剛」次類型,並回溯至戰後轟動一時的《天字第一號》(1946)。張建德則提出一種非傳統的觀點,指出《聊齋》鬼片具有冷戰寓意。研究對象,包括李翰祥改編自〈聶小倩〉的《倩女幽魂》(1960)、胡金銓改編自〈俠女〉的《俠女》(1970-71),以及徐克監製的〈聶小倩〉版本《倩女幽魂》(1987),都改編自蒲松齡的《聊齋誌異》。
附錄部分,收入三篇文章,分別是:影人座談會的討論紀錄;許敦樂有關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如何反映意識形態鬥爭的發言稿,許曾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以及由台灣學者左桂芳為香港電影資料館整理自由總會資料的工作報告,均具參考價值。在座談會的討論紀錄中,幾位代表左派陣營的講者,包括朱克、許敦樂、劉德生的發言甚值得注意,他們對左派的政治標籤很有保留,這種標籤對於釐清一些灰色地帶,並無幫助,這正好回應了本書前面幾篇文章所提到的問題。表面上是宿敵,其實暗地裡可以變成合作伙伴;這一刻大家還言笑晏晏,未幾卻又磨刀霍霍。政治、商業與文化,往往糾纏不清。
本書收錄的文章,除張濟順和左桂芳外,均源自文首所提及的研討會暨影人座談會。該研討會從2005年中開始籌備,得到香港大學中國研究策略研究專題(Strategic Research Theme on China Studies)和香港電影資料館提供研討會所需經費。當時參加籌備工作的,除編者二人外,還有何思穎、吳詠恩和容世誠。是次研討會能夠順利舉行,還有賴下列人士的支持,包括:朱克、吳俊雄、李小良、李元賢、李焯桃、汪朝光、黃紹倫、黃淑嫻、盛安琪、馮淑貞、焦雄屏、葉月瑜、葉漢明、葉嘉安、楊奎松、劉成漢、劉德生。
最後,要感謝本書各位作者,沒有他們的熱情參與,本書難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