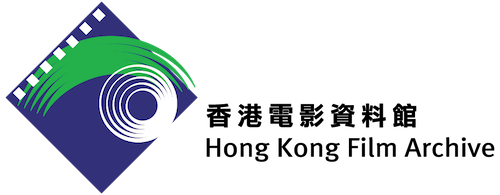張徹──回憶錄・影評集
懷念張徹──代序一
張徹先生原籍浙江,每當他講廣東話的時候都很有娛樂性,有時令我們連帶一眾演員和武師都笑得眼淚直流。例如他把「偷襲」說成是「偷食」,就教我們猜了大半天才弄懂是甚麼意思,可是張徹卻不以為忤,還跟着我們一起笑得開心,就如一位可親可敬的長輩,親和地看着一群頑劣的小孩在搗蛋。但當他講述鏡頭拍攝時,我們都不敢掉以輕心,更會付出百份之百的精神、努力和心思,克盡己能地完成該要做的工作,因為我們對張徹導演是百份之百的尊敬。他所設計的每一個鏡頭都是一種挑戰、一個學習的過程,也讓我們常常覺得,能夠在張徹的電影裏有着自己小小的貢獻,有一種不可言喻的自豪感,如若我們之中有誰做得不夠好的,他非但不予以責難,還加以激勵和指引,因他只注重每個人的長處,從不在乎別人的短處。在這個凡事令人壓力深重,欠缺安全感,人事鬥爭激烈,經常為了成敗得失而至精神緊張的電影生涯中,他能夠讓我們覺得拍電影是一種樂趣、一種境界,活得有尊嚴,令人對片場生活有種強烈的歸屬感。
張徹先生在其年輕時雖曾從事過短暫的政治生涯,但他的電影和行事為人卻一點也不「政治」。他有藝術家的浪漫,知識份子的風骨;為人坦蕩,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虛懷若谷兼有容人的雅量,卻沒有如一般政治家的權謀和機心。張徹又從不多言,也從不虛言。他把該說的話都放在電影和文字裏,他那揮灑自如的影像結構和文字運用都有着極強的思想性和感染力,每每流露出他的真性情、真性格。他的電影說的是大仁大義,又兼顧到人之常情,有武亦有俠,氣度恢宏而又從容不迫,看後每有令人蕩氣迴腸的痛快感。
張徹閒話少說,卻愛才、惜才,又能慧眼識英雄,曾跟他合作無間的編劇家倪匡和邱剛健、武術指導唐佳和劉家良、攝影師宮木幸雄以及一眾幕後功臣,都是深具名望和創意的一時俊彥,在張徹的電影中有着巨大貢獻。我等後輩在向張徹學習導演技巧的同時,又能從他們那裏學習到編劇在一部電影中的靈魂作用,而唐、劉兩位師傅更把中國武術的精華、神韻和意境,推陳出新,結合着強而有力的影像設計,構成一種獨特的動作美學,很能配合張徹的浪漫思維。
張徹更有塑造明星的超凡能力,他不但觀人於微,很能發掘出每一個人的潛質,而且他的直覺素來都非常準確。經他一手提拔及悉心栽培過的明星演員,好些都曾紅極一時,成為眾多青年男女所崇拜的偶像。他是用愛心、智慧和惺惺相惜的態度來栽培他的演員,又能根據各人不同的特質、潛能和吸引力而度身設計出不同的性格、獨特的形象,如王羽、羅烈、姜大衛、狄龍、王鍾、陳觀泰、傅聲、李修賢、郭追等都各具魅力,各有特色。他不但能塑造明星,也能令每一位演員都盡情發揮其所長,可謂伯樂適逢千里馬。
在早期的電影圈,很看重「老經驗」,年輕人往往被忽視,然而張徹卻獨愛提拔年輕人,重視年輕人。從年輕人中,他感受到那份豐沛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正如他電影中的主人翁都是英雄出少年,有少年人的浪漫,而在浪漫之餘,又帶有古之俠者的正義和正氣,能面對任何挑戰,肯定自我。在我跟隨張徹之前,我的個性比較害羞、木訥,又頗為自卑,對自己沒有多大信心,有意念、有感想也不敢說出來。但自從看了張徹的一系列電影如《獨臂刀》(1967)、《金燕子》(1968)、《遊俠兒》(1970)和《報仇》(1970)等片之後,使我覺得我也可以擁有那份少年的浪漫。正當我感到迷失,看不清自己和未來的時候,他卻鼓勵我應該專心向導演方面發展,而在當時來說,年青人做導演簡直是個不可能的夢。雖然我們之間平時話不多,但他知道我的潛能,他不但替我找到了方向,還幫助我建立自信,找到肯定自我的價值。想來,我不僅從張徹啟發到做導演的心得,也學習到做人處世之道,實屬感激。
張徹的電影永遠都有一份年輕的感覺。他忠於自己,堅持理想,一直到老仍然保持着年輕的創作心境。他思路仍然清晰,筆耕不輟,仍不忘扶掖後進,且每天都在惦掛着一群他曾經悉心栽培、視同己出、愛之殷切的演員和工作人員,令人為之肅然起敬。從六十年代伊始直至八十年代後期,他勇於破舊立新,用現代的觸覺和電影技巧,突破了傳統香港電影的老舊模式,首創陽剛武俠,其一系列的浪漫武俠片經典不但引發新潮,且開創了香港電影的武俠新世紀;其獨特的拍攝風格和豪快而富節奏感的動作設計,更影響了為數眾多的海內外電影工作者,從而也改變了香港電影的命運,使世人從此對港產片有全新的觀感和評價,直讓我等後輩感到興奮,引以為豪。
誠然,張徹先生在香港和中國的電影史上,有極其重要和肯定性的地位,其作品所發揮的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我們深深敬佩張徹先生的電影風格和風骨,感激他曾經拍攝出不少永垂不朽的電影,成為我們的典範,也留給我們永恆的美好回憶,實不愧為一代電影宗師。
吳宇森
二零零二年九月寫於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