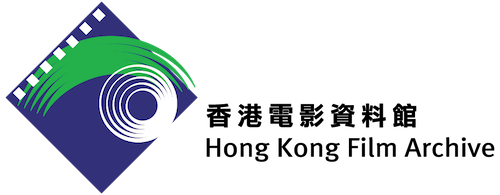故園春夢——朱石麟的電影人生
序言
朱石麟(1899-1967)的電影生涯橫跨三十餘年,從三十年代上海「聯華」,歷經孤島時期和敵偽的「中聯」「華影」,到戰後南來香港的「大中華」、「永華」、「龍馬」和「鳳凰」「長城」等不同階段,中間幾乎從沒間斷,編導過逾百部作品。早於八十年代初,香港的評論便已對他另眼相看,林年同稱他為中國電影一個舉足輕重的藝術家,舒琪對他早期電影語言的富實驗性和靈巧多姿感到驚訝,劉成漢稱頌他為中國古典電影的代表,而陳耀成則說他可能是中國電影史上最早的世界級導演,其畢生的作品構成了一個有關聯性、發展性的整體
1。
朱石麟由首次編導短片《自殺合同》(1930)開始,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正式展開,一直都留在聯華,沒有東張西望。這大抵跟他穩重的性格有關,而聯華亦的確提供了一個相對理想的製作環境。在他同輩的聯華導演中,孫瑜氣象開朗活潑,三十年代每一部作品都個性突出,自成一家,可惜戰時東遷西移,從武漢的「中製」(中國電影製片廠)、重慶的「中電」(中央電影攝影廠)、到北溫泉的「中教」(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期間只完成了《長空萬里》(1939)、《火的洗禮》(1941)兩部故事長片。戰後,籌拍經年的《武訓傳》(1951),卻成為了政治鬥爭的祭品,接著下來的創作難免元氣不足,令人扼腕。蔡楚生的作品社會意識強,一直受到左翼評論的激賞,戰時因處境危險,南下香港,完成了《孤島天堂》(1939)、《前程萬里》(1941)等國防電影。其後又輾轉逃難,及戰後重返上海,拍出了被正統電影史學家視為中國電影典範之作的《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49年後,他因事務和健康的關係,卻只拍了一部《南海潮》(1963),1967年其妻陳曼雲因被誣為特務而入獄,翌年蔡楚生抱憾而歿。吳永剛是同輩中極富探索精神的一員,處女作《神女》(1934)簡潔現代,一鳴驚人;《浪淘沙》(1936)無論從題材與風格都走在時代之先,當年卻被左翼評論批判得體無完膚。孤島時期他拍了不少影片,可惜現在能夠看到的很少,戰後拍攝的幾部影片也不知道是否還有拷貝。49年後的兩場大劫——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他都被捲了進去,幸好他的兩部戲曲電影《碧玉簪》(1963)和《尤三姐》(1966),仍顯大將之風。費穆的氣質跟朱石麟相近,在藝術的追求上卻比較大膽執著,遺憾的是,他的作品能夠完整保存下來的不多,還好《小城之春》(1948)已足以一錘定音,但從研究角度來看,畢竟少了點對照的參考。
相對這班傑出的同輩,朱石麟給人的感覺顯然比較老成平穩,但細看他一路走下來的創作軌跡,就會發覺他是中國電影裡難得一見的「作者」。這倒不是說上述幾位導演的藝術個性不強,而是他們受到太多時代的干擾,創作道路崎嶇迂迴,其間很多斷裂的地方,抗日戰爭所帶來的顛沛流離和創作上的制肘、49年後的文藝政策以及隨著而來的政治運動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窒礙了他們的電影之路。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三十年代的中國電影如此有活力,而其後卻顯得步履蹣跚,後繼乏力。相對而言,朱石麟戰時滯留上海,戰後南來香港,滿懷委屈,但從創作的角度來看,倒因禍得福,電影事業幾乎從沒斷裂過。他雖然當初跟正統的左翼電影並不合流,倒在殖民地的香港,成為了左派電影的旗手,這也許是歷史的諷喻。
從現在還能夠看得到的《戀愛與義務》(編劇,1931),到最後在香港完成的《故園春夢》(1964),朱石麟沒有刻意迎合時代大潮,每每以委婉順應的姿態發揮堅韌的實力,奇蹟般在歷史的狂瀾中創作不斷
2。近年來出土的作品多了,特別難能可貴的是,編者和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幾位同事在這一兩年中有機會補看了幾部他攝於上海淪陷時期的影片(如1942年的《博愛》、1943年的《良宵花弄月》和《萬世流芳》、1944年的《現代夫妻》),更確定他是中國電影裡少有的一名「作者」,其作品體現了極其統一和貫徹的母題和風格。三十年代在氣象開朗的上海,他並不特別熱衷表現進步,卻體恤著時代的關懷,躑躅游移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四十年代在齷齪壓抑的淪陷區,他埋首在密封的夢工場裡,編織著男女夫妻間的小故事,磨練得一身精巧綿密的技藝;五六十年代在荷戟徬徨的香港,他戰戰兢兢地經營著「鳳凰」這片小小的花圃。從開始時的素樸單純,到晚年的深沉悲絕,他的電影軌跡同時也是一代中國知識份子從希望、調節到幻滅的過程。難得的是,他似乎一直都保持著一份清醒與信念。
自從1983年香港國際電影節出版的《戰後香港國、粵語片比較研究──朱石麟、秦劍等作品回顧》以後,相隔了十多年才多了一本關於朱石麟電影的書,那就是1999年由朱石麟後人朱楓、朱岩編撰的《朱石麟與電影》。他們以子女身份憶述其父的一生,並收錄了多封家書,讓讀者得以一窺朱石麟在香港時期的私人世界,讓我們對他的處境多一層了解。除此之外,我們在香港再沒有看到對朱石麟進一步的探討,倒是2005年在北京出版的第五期《當代電影》,策劃了一個朱石麟特輯,重新審視朱石麟對中國電影和香港電影的影響,主持人是資深的電影史學家李少白,作者包括內地的趙衛防、李道新、盤劍、陳墨和香港的羅卡。在前述的研究基礎上,本書的作者們從歷史、文化和美學等多層面作出一些新的探討,確立朱石麟在中國電影史上的位置。
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感謝朱石麟先生的後人——朱楓女士和朱岩先生兩位。他們不但接受了我們的訪問,還把家中收藏多年的朱石麟遺物捐贈給香港電影資料館,我們在本書中收錄了其中四個從未出版過的劇本。孤島時期的影片資料非常缺乏,《香妃》(1940)、《龍潭虎穴》(1941)二片的劇本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參考;《生與死》(1953)的編劇是朱石麟的愛徒岑範,影片拷貝已散佚;而《楊貴妃》則抄錄於四十年代末,從沒拍成電影。從這次資料館舉辦的朱石麟電影回顧展以及這些補遺的文獻資料中,我們得以比較全面地看到,在動盪不安的大環境裡,一個藝術家深藏不露的探索、委曲求全的調節,以至心枯力竭的回歸歷程。書中也收錄了多年前岑範導演接受資料館同事訪問的記錄;近聞岑先生已於2008年1月23日作古,謹借此小小方角向他致敬。
黃愛玲
2008年2月12日
註釋
- 林年同、舒琪、劉成漢諸君的文章,請參看舒琪編:《戰後國、粵語片比較研究——朱石麟、秦劍等作品回顧》(第七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回顧特刊),香港:市政局,1983;陳耀成的〈流鶯隔世聽——追摹朱石麟〉一文,原載《電影雙週刊》,第112期,1983年5月26日,頁25-30,其後收錄於陳耀成:《最後的中國人》,香港:素葉出版,1998。
- 從電影經歷來說,跟朱石麟差不多同期的岳楓(1910-1999),可以拿來與之作一比較。岳楓於二十年代末踏入電影界,三十年代執導了兩部由陽翰笙編劇的作品《中國海的怒潮》(1933)和《逃亡》(1935),深受左翼評論讚賞。戰時留滬拍電影,處境跟朱石麟相仿。戰後來港發展,先後為長城、電懋和邵氏等公司拍片,最後一部影片是《惡虎村》(汪平合導,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