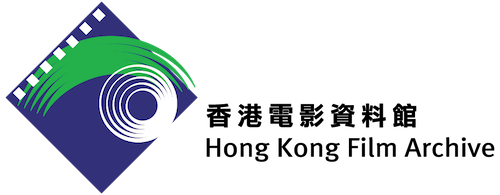「國泰人.國泰事」套裝之《有生之年──易文年記》
前言
大多數人認識的易文(原名楊彥岐,1920-1978),是電懋的導演和編劇,但他同時也是多產的填詞人,為自己和別人的電影插曲填詞。此外,他也是小說家和專欄作家,曾在香港的報刊上寫連載小說和專欄。說起來,他可算是今天香港多棲文人的先驅。易文來自舊學根底深厚的文人世家,自小就接觸詩詞、古文、書法、篆刻,可說是家學淵源。生於民國初年,他也受到西方文藝的影響,早年已經接觸新文藝,開始寫小說、散文,也看電影,並且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終生不渝。這樣一個中西交匯的背景,讓他成為一個具有多重身份的文人。
今天我們能夠在電影以外,從新認識易文,得感謝他從小培養的寫日記的習慣。儘管青年時代的他對於「寫日記」並不當一回事,但是父親對他殷殷期許,給他買來日記本1,也許不願辜負父親的好意,日記還是一天一天的寫下來了。青少年時代的易文,曾寫滿了多少本日記簿,由於多年的流離散佚,現在已無法深究了。但是從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末逝世為止,易文倒也沒有停止過寫日記。
數年前易文的長子楊見平先生跟香港電影資料館聯絡,表示藏有一批父親的日記、一本自傳體年記和照片及大量相關文獻,願意捐贈給香港電影資料館保存,並答允將年記公開出版。因著這份難得的因緣,我們有機會看到二十多本袖珍小型日記及易文自題為《有生之年》的年記手稿,對於研究者來說,這無異是一個寶藏。香港的電影人似乎不太喜歡將自己的電影生涯紀錄成文,像黎民偉、張徹與李晨風,能夠留下親筆的文字史料的,有如鳳毛麟角。因此面對著這一堆日記,各位同事的興奮心情,可想而知。並非要在其中發掘出甚麼秘聞軼事,更大的期望是,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日記本裡,留給我們一個怎樣的易文。
在整理年記的過程中,發現易文對於事件的記載,極為準確,除了記憶力之外,大概那些袖珍日記本也為他提供了不少資料參考。可是年記到底並非自傳,也許更像年譜,只將當年的人和事,擇其重要而記之。而所謂重要,自然是由當事人來決定了。年記由易文出生那一年開始,記述家境與父母,還有當年種種政治與時事,設定了自己來到人間的歷史舞台,然後按年記敘,直到一九七七年,年記遽然而止,大概當時他的健康已經轉壞,無法再記下去了。
事件的發生少不了人,年記中記下了大量的人名,有不少是易文的父親楊千里先生交遊的軍政名人與藝術家,當然還有後來易文由報界轉業電影,從電懋到邵氏的事業轉折,到經歷結婚生子以至抱孫子,甚至幾段紅顏知己的情緣,都毫不諱言地錄於年記內。易文早年曾做記者和編輯,對於自己的人生,也彷彿報道新聞故事一般,重點在客觀的時、地、人、事,卻絕少月旦評論,但他總是記得與家人和朋友相處時的快樂時光。由於年記中人物繁多,除部分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外,其餘與楊氏父子交遊的人物,都盡可能加上註釋,對其生平略作介紹,讓讀者對這個人際網絡有個概括的印象。這些人讓我們看到當年楊氏父子「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社交圈子,反映的不單是二人的交遊廣闊,同時也是自民初以來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側影。由於牽涉的人物,來自不同的背景,編寫註解時,有「書到用時方恨少」的惶恐。疏漏在所難免,但編者亦責無旁貸,唯有期望識者指正。
至於年記中提及的親密女友,由於其中有幾位現仍健在,而且是為人認識的公眾人物,為了避免為她們的生活遭受不必要的騷擾,年記中將這些女士的名字隱去。原來當年易文逝世不久,太太周綠雲女士即在遺物中發現這一本年記,並打算連同易文其他遺作出版「易文全集」。這件事後來擱置了,據台北的黃仁先生相告,原因正是為了不想因年記的出版,影響了其中提及的女士們。年記於是一直被收藏起來,直到楊見平先生跟香港電影資料館聯絡,於是才又有了跟讀者見面的機會。
除了年記部分,本書亦收錄了多篇易文早年發表的文章,還有好友對他的悼念,與年記一併閱讀,對他的為人會有更全面的瞭解。此外,楊見平以兒子的身份,記述對父親的種種印象,幽默生動而別有見地,可以想見父子之間的深厚感情。李培德從國共冷戰與香港電影人的角度來解讀易文的年記與袖珍本日記,分析詳盡,讓人從另一層面理解冷戰年代中,香港電影與兩岸以至南洋的關係。黃愛玲則將易文的「牌友」張徹與易文的生平作比較,指出不同的人生歷練造就了兩人截然不同的藝術風格,也點出了易文一貫「兒女情長」的性格──他記下的,盡是父母子女夫妻與情人之間的種種,並且將之一一投射到他的電影裡。
每次出版新書,都是一個全新的學習過程,今年也不例外,而且範圍逸出了自己向來熟悉的電影,一頭栽進了中國近代史中,其實已經比較接近歷險了。可幸在這歷險中不乏良師益友,黃愛玲就這書的結構提出意見,李培德解答了許多關於研究歷史文獻的問題,台灣的黃仁更給我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這些都是編書過程中的鼓勵。還有各位同事有形無形的支持,謹在此一併謝過。
藍天雲
2009年3月3日
注釋
- 易文以本名楊彥岐寫的文章〈二十散記〉裡有這樣的話:「……每個新年,我總買一本日記簿。但是,我不會按日記下自己的遭遇和心情──太興奮了不屑記,太冷落了記不出,結果是瞎塗亂寫,有時抄一段讀到的好詩,有時寫幾句自鳴得意的雋句。日記簿破了、丟了,於是又買新的。今年父親給了我一本五年日記,每天空白地位不多,不夠瞎塗亂寫, 只好下一個決心,等高興的時候,再寫一些。」原刊《宇宙風》乙刊第二十一期 , 1939 年 2 月,頁 150-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