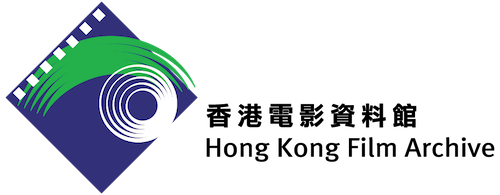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
序言
香港電影資料館自一九九六年以來,已做了超過二百個影人的口述歷史訪問。去年出版了第一本口述歷史叢書《南來香港》,從前輩的口述經歷中,我們很清晰地看到了香港電影與中國電影千絲萬縷的關係。香港電影本來就應該是中國電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只是由於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的分歧,中國電影史學者從來不把香港電影放在眼裏,直到近年,內地才興起一股香港電影熱潮,坊間亦出版了不少論述香港電影的書籍;反過來說,香港電影評論界也往往抗拒與中國歷史的大傳統扯上關係,努力建構一種獨立的地方觀點,香港國際電影節歷年來的香港電影回顧部份倒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早年的《戰後香港電影回顧1946-1968》(1979)、《戰後國、粵語片比較研究──朱石麟、秦劍等作品回顧》(1983)、《香港電影的中國脈絡》(1990)、《香港──上海:電影雙城》(1994)等。
《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承接上一冊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的脈絡,透過對九位前輩影人的訪談,勾勒出香港與中國大陸電影之間微妙的關係。他們包括曾為中國有聲電影拓荒的陸元亮、五十年代初被香港政府以莫須有罪名驅逐出境的舒適、由江南小城翩然降落東方之珠的韋偉、能演能編能導的鮑方、長城大公主夏夢、擅拍喜劇的胡小峰、藝途坎坷的編劇朱克、著名攝影師羅君雄和鳳凰當家花旦朱虹。因緣際會,他們都於五十年代參加了當年有左派背景的長城和鳳凰,因而與其他相同處境的影人被標籤為「左派影人」。不少香港人聞「左」色變,卻忘記了在歷史的大洪流中,「左」的思潮曾經寄託了一代人對家國和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想與憧憬。究竟「左」的內容是甚麼?上述影人如何體現這種時代的精神?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他們如何自處?經過歷史的轉折,他們又怎樣回看往昔?透過前輩們的訪談,抽象的概念變得立體起來,「左派影人」不再是想像中橫眉倒豎的政治動物,而是有着常人一般的喜怒哀樂。
由於篇幅所限,「長、鳳、新」中我們權宜暫且先集中於長城、鳳凰這兩家背景比較接近的國語片公司,至於拍攝粵語片的新聯,則要留待另一次機會了。事實上,即使是「長、鳳」中人,還有很多未及訪問,譬如一九六七年曾站在「反英抗暴」前線而被香港政府未經審訊囚禁年多的石慧、傅奇夫婦,就一直未有機會聯繫上。朱石麟是鳳凰的靈魂人物,幾乎每一個受訪者都會提及他,可惜斯人早已作古,值得慶幸的倒是他的後人朱楓、朱岩兩年前編寫了《朱石麟與電影》一書1,資料豐富,甚具參考價值。袁仰安是早期長城的關鍵人物,五七年因複雜的內部人事問題而脫離長城,另組新新影業公司,一直以來,在有關這一段歷史的文獻中,他都沒受到應有的重視2;他於一九九四年去世,我們曾訪問過他的夫人蘇燕生、女兒毛妹以及大女婿沈鑒治,但資料反不及沈鑒治於一九九七年在《信報》連載的〈舊影話〉詳盡,現將該文收入本書,希望能起到補遺作用。
從永華到長城
抗戰之後,中國局勢未轉穩定,倒日見緊張,不少上海影人南來香港。一九四七年,身家雄厚的李祖永便在「製片大王」張善琨的協助下在香港創辦永華影業公司,開業之作《國魂》(卜萬蒼導演,1948)投資百萬,聲勢浩大,緊接着拍攝的《清宮秘史》(朱石麟導演,1948)亦製作嚴謹,展現了過人的氣魄。與此同時,因時局關係而南來香港的一批左翼影人亦各自乘勢建了幾家有進步傾向的公司,互相串連,共同發展他們的抱負和事業,其中包括大光明、南群、南國、大江、民生等電影公司。
到了一九四九年,李、張意見不合,張善琨另起爐灶,組織長城影業公司,主要人事安排如下:總經理袁仰安、經理胡晉康、廠長沈天蔭,而張善琨則一如永華時期,仍居幕後策劃。在六十年代擔任過清水灣片廠廠長的陸元亮,自三十年代上海新華影業公司時期起便與張善琨緊密合作,戰後更親身經歷了永華的興衰,跟張、李二人都有過共事的經歷,他在本書的訪談中,便對二人作出了非常直率的評價3。短短一年半內,長城出品了《蕩婦心》(1949)、《血染海棠紅》(1949)、《瓊樓恨》(1949)、《王氏四俠》(1950)、《一代妖姬》(1950)等影片,聲勢不凡,但此時國內形勢已大變,長城市場失據,財政失控,人事上的矛盾更日見尖銳化。一九五零年張善琨退出長城、公司改組,名稱改為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在這件事件上,張善琨的遺孀童月娟和袁仰安的家人各有各的說法:前者認為張善琨是因政治理由,「被掃地出門」,後者則將張、袁二人之分道揚鑣歸咎於「錢銀轇轕」4。五十年代於上海出版的《青春電影》半月刊對長城改組的事態發展,一直頗為關注5。據該刊報道,改組後的公司仍由袁仰安出任總經理之職,拉上香港《大公報》的經理費彝民參佐戎機,得到以航運業起家的呂建康全力支持,又羅致司馬文森為挑選劇本的顧問,也就是說,打從開始,新長城的左派背景已很清晰。
鳳凰的誕生
另一方面,永華既讓張善琨這個靈魂人物走掉,經濟上又不穩定,其後更因勞資糾紛發生了一次工潮,不少影人不得不另謀出路。這種艱難的處境,再加上那時候追求進步思想的社會氣候,便促成了五十年代影業公司的誕生,舒適在本書的訪談中對此便有提及。但它跟大光明、南群、南國等公司有所不同,它不是由老闆投資,而是一家合作社式的公司,以員工們的勞動力作為資本。五十年代成立一年,拍了兩部出色的影片《火鳳凰》(司馬文森編劇6,王為一導演,1951)和《神鬼人》(顧而已、白沉、舒適合導,1952),其經營模式和成功經驗對後來的「兄弟班」公司如鳳凰及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相信也起了很大的啟發作用;但一如其他幾家帶進步思想色彩的小公司,五十年代也沒有維持長久,新中國成立後的頭兩、三年裏,許多影人北上歸國,而留港的不少成員如程步高、劉瓊、舒適、李麗華、韓雄飛、胡小峰、白沉、韓非等,也轉到改組後的長城和稍後成立的鳳凰去了。
鳳凰的基本班底多來自龍馬影業和五十年代。龍馬是由企業家吳性栽投資、費穆主持的一家電影公司。吳性栽雖是商人,但對藝術素感興趣,對京劇尤其着迷,因其對京劇名角的大力支持而被稱為「京劇托勒斯」,他對電影的興趣亦早自一九二四年創辦上海百合影片公司開始。他跟費穆非常投緣,曾先後支持他拍攝周信芳主演的京劇戲曲片《斬經堂》(1937),以及梅蘭芳主演的彩色戲曲片《生死恨》(1948)。一九四七年,他另組文華影片公司,拍了多部出色的影片,其中包括費穆的《小城之春》(1948)。他於一九四八年僑居香港,五零年與費穆創辦龍馬,據韋偉說,吳性栽屬龍,費穆屬馬,故取其名7。費穆於一九五一年心臟病發逝世,吳性栽於翌年退出龍馬,內裏乾坤恐非我們局外人所能理解。在這個處境中,當時龍馬的骨幹朱石麟一方面集合原有員工接手管理,一方面籌組鳳凰影業公司,並於一九五三年拍了創業作《中秋月》。有別於商人出資的長城,鳳凰是一家與人合資組建的「兄弟」公司,並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8。
三十年代「左翼電影」的影響
要理解所謂「左派電影」在香港電影史上的獨特位置,大抵要走進時光隧道,從三十年代的上海說起。
一九三零年,中國共產黨組織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發起人有魯迅、郭沬若、茅盾、郁達夫、沈端先(夏衍)、錢杏邨(阿英)、田漢、鄭伯奇、華漢(陽翰笙)、沈葉沉(沈西苓)等五十餘人。一二八戰爭結束後不久,共產黨又成立了電影小組,由夏衍領導,不但向當時的電影公司提供具有「進步」內容的劇本,也介紹了許多以「左翼劇盟」為主的新派文藝工作者到各家影片公司去,更在報刊上建立評論陣地,推動左翼電影的創作。在中國電影的整體發展上,左翼思潮的作用是否被高估了,也許可以重新評價,但無可否認,它影響戰後的香港電影,則有跡可尋。
打從一九三三年左翼文人參加明星影片公司開始,他們即在公司內部以編劇委員會的形式,負責電影劇本的創作與修改,五十年代、長城和鳳凰等公司都參照了這種集體創作方式。據報道,長城於一九五零年改組後成立了一個編導委員會,由馬國亮、岳楓、李萍倩、劉瓊、顧而已、陶秦等任委員,討論劇本內容和演員分配的問題9。從這個名單看來,劇本創作仍掌握在真正電影人的手上,而左派組織的參與還傾向低調,連正牌屬於左派系統的司馬文森也沒有在名單上出現,倒隱沒於幕後。新成立的鳳凰亦有一個藝術委員會,由朱石麟主持,當時許多電影劇本都是在集體討論中產生的。曾在長城任編劇的朱克在訪談中說:「在左派公司,編劇的地位很高……有『人民劇作家』之稱,回到國內,非常受尊重。」與此同時,他們也有所謂「九稿十三綱」,浪費不少人力物力10。這種集體討論的方式誠然有優點也有缺點,長城另一編劇查良景在一次口述歷史訪問中便有相當中肯的說法:好處是經過反覆討論,作品的質素比較有保證,對新人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長城、鳳凰便培養了不少編導人才;壞處是往往在過程中犧牲了個性,因為藝術講求創新,而集體討論卻注重集中11。
從編導人才培訓這個角度來看,左派公司確有別樹一幟的機制,如收入本書訪談中的胡小峰、鮑方、羅君雄等都是內部培訓出來的,其他如陳靜波、傳奇、張錚、張鑫炎等都是從演員甚至剪接出身而晉升為導演的,而作為女性,任意之和朱楓亦獲得不少執導的機會,就連貴為第一線女演員的石慧也曾當過副導演,這些做法在其他同期的大公司如邵氏、電懋裏便不多見。長城是商人出資,早期集合了岳楓、李萍倩、程步高、黃域等資深上海影人,編導人才比較多,而早期鳳凰能獨當一面的卻只有一個朱石麟,對人才自然更加渴求。鳳凰很多出品都掛着朱石麟「總導演」之名,而實際執行的則是聯合導演的新人,幾部片下來,新人便可自立門戶,獨立執導演筒了。曾接受訪問的影人,從演員到導演,幾乎無人不提及朱石麟在這方面的貢獻,但從另一角度看,這種眼睛只向內看的做法卻又難免封閉。左派公司甚少向外界招攬編導人才,自然也較少受到外間的衝擊。這一點跟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界政治立場的壁壘分明不無關係。
影圈左右陣營的關係
中國政權易手後,香港政府對左派的影響力非常敏感,一九五二年初先後兩次將十名左派影人驅逐出境12。事過境遷,現居上海的舒適便在訪談中對親身經歷的過程有很幽默的描述。一九五六年,王元龍、胡晉康、張善琨等影人正式成立「港九電影從業人員自由總會」,翌年改稱「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所有電影若要在台灣發行,拍戲之前都要跟「自由總會」登記,沒有他們的證書,台灣方面不會通過,影片便不能在台灣發行。文革前,「長、鳳、新」甚至部份中聯的出品都可在大陸公映,據五、六十歲以上的國內朋友憶述,當年這些影片都相當賣座,甚至比國產片更受歡迎。這其中雙方實際經濟上的關係如何,我們局外人不得而知,宜作更深入的研究,但對「長、鳳、新」而言,肯定是很重要的支持。然而,這個龐大的市場對「非左派」系統的電影公司卻早已關上了大門13。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市場便顯得非常重要,除了「長、鳳、新」等直屬左派系統的影人外,其餘大部份人都要參加「自由總會」,包括當年的邵氏、電懋/國泰等大公司的工作人員。於是,左派公司即使有心向外界招手,左派系統以外的影人也礙着市場的考慮而不敢加入了;而且,左派公司員工的酬勞也遠遠不及其他公司。影響所及,「長、鳳、新」只好集中力量進行內部的人才培訓。
然而,「長、鳳、新」倒又不是跟外界絕緣的;事實上,他們跟其他電影公司有很多商業上的聯繫。五、六十年代,特別是五十年代初、中期,邵氏和電懋均未正式開發自己的製片事業,但他們在東南亞卻擁有龐大的戲院網絡,需要大量影片上映,「長、鳳、新」的影片製作嚴謹,明星有號召力,剛好填補這個空間。那個時候,電懋主要買長城出品,邵氏多買鳳凰作品,光藝則買新聯的粵語片,各適其所,各取所需。從五、六十年代出品的所謂左派電影看來,中共似乎無意在香港大搞意識形態的活動,只是希望在這個小島上維繫着一個據點,與外界作有限度的溝通。
細看影片的內容,當然部份作品(特別是五十年代早期)反映了戰後香港社會的現狀及當時的理想主義色彩,但充其量只是以嬉笑怒罵的方式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矯飾(如《說謊世界》,1950和《百寶圖》,1953),或在片末隱含着返回「鄉下」的號召(如《江湖兒女》,1952和《一板之隔》,1952),或委婉地將希望寄託於平民教育的興辦上(如《寸草心》,1953和《姊妹曲》,1954)。更多的作品倒是充滿着小資產階級的溫情與趣味(如《三戀》,1956、《情竇初開》,1958和《眼兒媚》,1958等),在寫及現代婦女的處境時(如《我是一個女人》,1955、《新寡》,1956、《寂寞的心》,1956),也總是一方面表現出對個性解放的渴求,另一方面卻又不敢太背離保守的社會氣候,今天看來,作品往往因而顯得有點尷尬。及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香港電影踏入了國語片的旺盛期,邵氏、電懋、長城、鳳凰等公司百花齊放,左派電影的題材也越來越多樣化,從夏夢主演的上海越劇電影系列(《王老虎搶親》,1961、《三看御妹劉金定》,1962、《金枝玉葉》,1964)到傅奇、張鑫炎導演的新派武俠片《雲海玉弓緣》(1966),從改編文學名著的《故園春夢》(1964)到遠赴蒙古拍攝的俠義傳奇片《金鷹》(1964),從諷刺喜劇《樑上君子》(1963)到愛情小品《含苞待放》(1966),「長、鳳」的路線與毛澤東「廷安講話」的精神相去甚遠。
政治與電影
從另一方面看,經過「長、鳳」成立之初一段相對平靜的日子後,國內的政治浪潮似乎開始影響香港左派影圈。袁仰安拍攝改編自魯迅名著的《阿Q正傳》(1958),並沒有得到國內的支持,影片尚未正式完成,他便於一九五七年離開長城,另組新新影業公司,《阿Q正傳》最後由新新發行14;編劇朱克於本書的訪談中說:「國內大概從一九五四年開始派人來長城。黨來了,袁仰安便要走。」這裏提及的年份可能不太準確,畢竟已差不多是半個世紀前的事了。朱克本人於一九五八年被長城開除,當時國內正進行反右運動,這幾件事不知是巧合,抑或反映了國內形勢對香港左派影圈的影響。
然而,國內的十年文革,卻肯定對香港左派電影事業造成了不能逆轉的破壞,這一點,幾乎每一位受訪者都意見一致。在那天翻地覆的歲月裏,有人情緒激昂,裘萍便在一次訪問中坦然承認當時參與其事的投入15;石慧、傅奇夫婦亦積極參與當年的「反英抗暴」,傅奇是「鬥委會」第一批公佈的成員之一,夫婦二人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凌晨二時在家裏被拘捕,囚禁了一年多才獲得釋放16。也有人打從開始就不贊成文革,長城大公主夏夢當時剛巧懷孕,便藉此不參加左派組織的遊行集會,更於一九六七年九月悄然離開香港,遠赴加拿大,兩年後回港,卻從此不與電影界交往,直到十年後才重回電影圈,組青鳥電影公司,監製了《投奔怒海》(許鞍華導演,1982)、《自古英雄出少年》(牟敦芾導演,1983)和《似水流年》(嚴浩導演,1984)等三部影片。在這場政治運動中,大抵更多人是心懷疑惑,卻又無法置身事外,鮑方便是其一。在本書收錄的訪談中,鮑方坦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他也拍了一些很「左」的影片,如《沙家浜殲敵記》(1986)和《大學生》(1970),其後便無以為繼;一九七四年開拍的《屈原》,直至一九七七年打倒四人幫後才正式上映。之後,「長、鳳、新」已不能恢復五、六十年代的元氣,一九八二年三家公司合併,組成銀都機構,一直到今。
結語
本地人士對香港「左派電影」的研究不多,已發表的文章也較零散。第三屆香港國際電影節(1979)的《戰後香港電影回顧1946-1968》對戰後的進步電影作出了初步的探討,第七屆香港國際電影節(1983)的《戰後國、粵語片比較研究──朱石麟、秦劍等作品回顧》更進一步,其中石琪的〈六十年代港產左派電影及其小資產階級性〉是少數直接討論左派電影的文章。第九屆香港國際電影節(1985)有「李萍倩紀念特輯」,對其電影事業的發展及作品作出了初步研究。第十四屆香港國際電影節(1990)的《香港電影的中國脈絡》,有多篇文章探討香港電影中的中國因素,其中論及香港左派電影的有羅卡的〈傳統陰影下的左右分家〉和湯尼‧雷恩的〈轉向的擁抱──中共對中國電影的改造及其在香港的迴響〉;第十八屆香港國際電影節(1994)的《香港──上海:電影雙城》論及上海左翼影人在港的發展,並介紹了多部李萍倩在香港時期的作品。一九七八年沈西城編著、翁靈文校訂的《香港電影發展史初稿》中有一章寫長城的崛起,其中對舊長城到新長城的轉折有比較詳細的描述,對袁仰安的角色也有記載17。九十年代中,廖一原、馮凌霄、周落霞、吳邨等合寫的〈香港愛國進步電影的發展及其影響〉18;陳文、薛后合寫的〈香港早期粵語片簡述〉19,以及周落霞、馮凌霄、余倫合寫的〈「銀都」的成立及一些較有影響的作品〉20等三篇文章,對香港左派電影的來龍去脈作了較有系統的概括,卻對袁仰安這個人物刻意迴避。
我們希望這本影人口述歷史叢書能引起大家的興趣,摒除成見,重新審視這段歷史,作出比較有系統的研究。在這裏,謹衷心感謝所有接受電影資料館影人口述歷史訪問的前輩們,您們的憶述令一段被埋沒良久的歷史又活了過來,就如同在灰撲撲的底板塗上了豐富的色彩。
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
黃愛玲
2001年9月7日
註釋:
- 朱楓、朱岩編著:《朱石麟與電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 參看廖一原、馮凌霄(執筆)、周落霞、吳邨:〈香港愛國進步電影的發展及其影響〉,收錄於蔡洪聲、宋家玲、劉桂清合編:《香港電影80年》,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
- 參看本書〈陸元亮〉一章。
- 參看黃愛玲:〈童月娟:新華歲月〉,郭靜寧編:《南來香港》(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1),香港電影資料館,2000;另參看本書的〈舊影話〉。
- 詳見《青春電影》半月刊,上海,1950年3月1日第5期至1950年5月15日第11期。
- 余慕雲:《香港電影史話》第四卷,香港,次文化堂,2000,21至23頁。
- 黃愛玲編:《詩人導演──費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1998,204頁。
- 參看廖一原、馮凌霄等前引文章及本書〈韋偉〉一章。
- 《青春電影》半月刊,上海,1950年5月15日,第11期。
- 參看本書〈朱克〉一章。
- 摘自查良景(香港電影資料館影人口述歷史訪問),1997年4月1日。
- 1952年1月10日,香港政府入屋拘捕並驅逐了司馬文森、劉瓊、舒適、齊聞韶、楊華、馬國亮、沈寂及狄梵等八名電影工作者出境;五日後,白沉、蔣偉相繼被遞解出境。
- 早於1950年,中國政府已對電影事業嚴加管制,是年文教廳文化事業管理處禁映的影片便有八十餘部,內有國語片十二部,包括《大涼山恩仇記》、《血染海棠紅》、《莫負青春》、《黃天霸》、《一夜皇后》、《國魂》、《兩代女性》、《人海妖魔》、《鳳還巢》、《奇女子》、《水滸傳》、《血濺姊妹花》等,詳見《青春電影》半月刊,上海,1950年3月1日,第5期。
- 詳見本書沈鑒治之〈舊影話〉。
- 摘自裘萍(香港電影資料館影人口述歷史訪問),1998年5月29日。
- 可參考〈新聞專題:六七暴動秘辛〉,《經濟日報》,2000年11月28日及
- 沈西城編著、翁靈文校訂:〈香港電影發展史初稿〉之四,《新觀察》月刊,香港,第七期,1978
- 同註2
- 收錄於薛后:《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0。
- 1996年中國台港電影研究會在廣州召開的「香港電影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