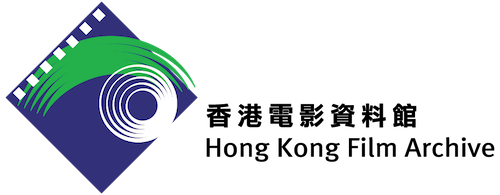「国泰人.国泰事」套装之《有生之年──易文年记》
前言
大多数人认识的易文(原名杨彦岐,1920-1978),是电懋的导演和编剧,但他同时也是多产的填词人,为自己和别人的电影插曲填词。此外,他也是小说家和专栏作家,曾在香港的报刊上写连载小说和专栏。说起来,他可算是今天香港多栖文人的先驱。易文来自旧学根底深厚的文人世家,自小就接触诗词、古文、书法、篆刻,可说是家学渊源。生于民国初年,他也受到西方文艺的影响,早年已经接触新文艺,开始写小说、散文,也看电影,并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终生不渝。这样一个中西交汇的背景,让他成为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文人。
今天我们能够在电影以外,从新认识易文,得感谢他从小培养的写日记的习惯。尽管青年时代的他对于「写日记」并不当一回事,但是父亲对他殷殷期许,给他买来日记本1,也许不愿辜负父亲的好意,日记还是一天一天的写下来了。青少年时代的易文,曾写满了多少本日记簿,由于多年的流离散佚,现在已无法深究了。但是从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末逝世为止,易文倒也没有停止过写日记。
数年前易文的长子杨见平先生跟香港电影资料馆联络,表示藏有一批父亲的日记、一本自传体年记和照片及大量相关文献,愿意捐赠给香港电影资料馆保存,并答允将年记公开出版。因着这份难得的因缘,我们有机会看到二十多本袖珍小型日记及易文自题为《有生之年》的年记手稿,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无异是一个宝藏。香港的电影人似乎不太喜欢将自己的电影生涯纪录成文,像黎民伟、张彻与李晨风,能够留下亲笔的文字史料的,有如凤毛麟角。因此面对着这一堆日记,各位同事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并非要在其中发掘出甚么秘闻轶事,更大的期望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日记本里,留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易文。
在整理年记的过程中,发现易文对于事件的记载,极为准确,除了记忆力之外,大概那些袖珍日记本也为他提供了不少资料参考。可是年记到底并非自传,也许更像年谱,只将当年的人和事,择其重要而记之。而所谓重要,自然是由当事人来决定了。年记由易文出生那一年开始,记述家境与父母,还有当年种种政治与时事,设定了自己来到人间的历史舞台,然后按年记叙,直到一九七七年,年记遽然而止,大概当时他的健康已经转坏,无法再记下去了。
事件的发生少不了人,年记中记下了大量的人名,有不少是易文的父亲杨千里先生交游的军政名人与艺术家,当然还有后来易文由报界转业电影,从电懋到邵氏的事业转折,到经历结婚生子以至抱孙子,甚至几段红颜知己的情缘,都毫不讳言地录于年记内。易文早年曾做记者和编辑,对于自己的人生,也彷佛报道新闻故事一般,重点在客观的时、地、人、事,却绝少月旦评论,但他总是记得与家人和朋友相处时的快乐时光。由于年记中人物繁多,除部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外,其余与杨氏父子交游的人物,都尽可能加上注释,对其生平略作介绍,让读者对这个人际网络有个概括的印象。这些人让我们看到当年杨氏父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社交圈子,反映的不单是二人的交游广阔,同时也是自民初以来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侧影。由于牵涉的人物,来自不同的背景,编写注解时,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惶恐。疏漏在所难免,但编者亦责无旁贷,唯有期望识者指正。
至于年记中提及的亲密女友,由于其中有几位现仍健在,而且是为人认识的公众人物,为了避免为她们的生活遭受不必要的骚扰,年记中将这些女士的名字隐去。原来当年易文逝世不久,太太周绿云女士即在遗物中发现这一本年记,并打算连同易文其他遗作出版「易文全集」。这件事后来搁置了,据台北的黄仁先生相告,原因正是为了不想因年记的出版,影响了其中提及的女士们。年记于是一直被收藏起来,直到杨见平先生跟香港电影资料馆联络,于是才又有了跟读者见面的机会。
除了年记部分,本书亦收录了多篇易文早年发表的文章,还有好友对他的悼念,与年记一并阅读,对他的为人会有更全面的了解。此外,杨见平以儿子的身份,记述对父亲的种种印象,幽默生动而别有见地,可以想见父子之间的深厚感情。李培德从国共冷战与香港电影人的角度来解读易文的年记与袖珍本日记,分析详尽,让人从另一层面理解冷战年代中,香港电影与两岸以至南洋的关系。黄爱玲则将易文的「牌友」张彻与易文的生平作比较,指出不同的人生历练造就了两人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也点出了易文一贯「儿女情长」的性格──他记下的,尽是父母子女夫妻与情人之间的种种,并且将之一一投射到他的电影里。
每次出版新书,都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今年也不例外,而且范围逸出了自己向来熟悉的电影,一头栽进了中国近代史中,其实已经比较接近历险了。可幸在这历险中不乏良师益友,黄爱玲就这书的结构提出意见,李培德解答了许多关于研究历史文献的问题,台湾的黄仁更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这些都是编书过程中的鼓励。还有各位同事有形无形的支持,谨在此一并谢过。
蓝天云
2009年3月3日
注释
- 易文以本名杨彦岐写的文章〈二十散记〉里有这样的话:「……每个新年,我总买一本日记簿。但是,我不会按日记下自己的遭遇和心情──太兴奋了不屑记,太冷落了记不出,结果是瞎涂乱写,有时抄一段读到的好诗,有时写几句自鸣得意的隽句。日记簿破了、丢了,于是又买新的。今年父亲给了我一本五年日记,每天空白地位不多,不够瞎涂乱写,只好下一个决心,等高兴的时候,再写一些。」原刊《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一期,1939年2月,页15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