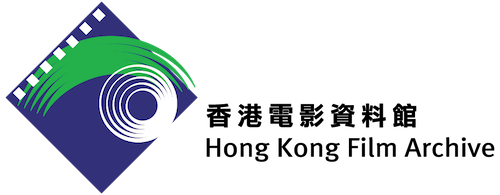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二: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
序言
香港电影资料馆自一九九六年以来,已做了超过二百个影人的口述历史访问。去年出版了第一本口述历史丛书《南来香港》,从前辈的口述经历中,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香港电影与中国电影千丝万缕的关系。香港电影本来就应该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只是由于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电影史学者从来不把香港电影放在眼里,直到近年,内地才兴起一股香港电影热潮,坊间亦出版了不少论述香港电影的书籍;反过来说,香港电影评论界也往往抗拒与中国历史的大传统扯上关系,努力建构一种独立的地方观点,香港国际电影节历年来的香港电影回顾部份倒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早年的《战后香港电影回顾1946-1968》(1979)、《战后国、粤语片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1983)、《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1990)、《香港──上海:电影双城》(1994)等。
《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承接上一册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的脉络,透过对九位前辈影人的访谈,勾勒出香港与中国大陆电影之间微妙的关系。他们包括曾为中国有声电影拓荒的陆元亮、五十年代初被香港政府以莫须有罪名驱逐出境的舒适、由江南小城翩然降落东方之珠的韦伟、能演能编能导的鲍方、长城大公主夏梦、擅拍喜剧的胡小峰、艺途坎坷的编剧朱克、著名摄影师罗君雄和凤凰当家花旦朱虹。因缘际会,他们都于五十年代参加了当年有左派背景的长城和凤凰,因而与其他相同处境的影人被标签为"左派影人"。不少香港人闻"左"色变,却忘记了在历史的大洪流中,"左"的思潮曾经寄托了一代人对家国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与憧憬。究竟"左"的内容是什么?上述影人如何体现这种时代的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们如何自处?经过历史的转折,他们又怎样回看往昔?透过前辈们的访谈,抽象的概念变得立体起来,"左派影人"不再是想像中横眉倒竖的政治动物,而是有着常人一般的喜怒哀乐。
由于篇幅所限,"长、凤、新"中我们权宜暂且先集中于长城、凤凰这两家背景比较接近的国语片公司,至于拍摄粤语片的新联,则要留待另一次机会了。事实上,即使是"长、凤"中人,还有很多未及访问,譬如一九六七年曾站在"反英抗暴"前线而被香港政府未经审讯囚禁年多的石慧、傅奇夫妇,就一直未有机会联系上。朱石麟是凤凰的灵魂人物,几乎每一个受访者都会提及他,可惜斯人早已作古,值得庆幸的倒是他的后人朱枫、朱岩两年前编写了《朱石麟与电影》一书1,资料丰富,甚具参考价值。袁仰安是早期长城的关键人物,五七年因复杂的内部人事问题而脱离长城,另组新新影业公司,一直以来,在有关这一段历史的文献中,他都没受到应有的重视2;他于一九九四年去世,我们曾访问过他的夫人苏燕生、女儿毛妹以及大女婿沈鉴治,但资料反不及沈鉴治于一九九七年在《信报》连载的〈旧影话〉详尽,现将该文收入本书,希望能起到补遗作用。
从永华到长城
抗战之后,中国局势未转稳定,倒日见紧张,不少上海影人南来香港。一九四七年,身家雄厚的李祖永便在"制片大王"张善琨的协助下在香港创办永华影业公司,开业之作《国魂》(卜万苍导演,1948)投资百万,声势浩大,紧接着拍摄的《清宫秘史》(朱石麟导演,1948)亦制作严谨,展现了过人的气魄。与此同时,因时局关系而南来香港的一批左翼影人亦各自乘势建了几家有进步倾向的公司,互相串连,共同发展他们的抱负和事业,其中包括大光明、南群、南国、大江、民生等电影公司。
到了一九四九年,李、张意见不合,张善琨另起炉灶,组织长城影业公司,主要人事安排如下:总经理袁仰安、经理胡晋康、厂长沈天荫,而张善琨则一如永华时期,仍居幕后策划。在六十年代担任过清水湾片厂厂长的陆元亮,自三十年代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时期起便与张善琨紧密合作,战后更亲身经历了永华的兴衰,跟张、李二人都有过共事的经历,他在本书的访谈中,便对二人作出了非常直率的评价3。短短一年半内,长城出品了《荡妇心》(1949)、《血染海棠红》(1949)、《琼楼恨》(1949)、《王氏四侠》(1950)、《一代妖姬》(1950)等影片,声势不凡,但此时国内形势已大变,长城市场失据,财政失控,人事上的矛盾更日见尖锐化。一九五零年张善琨退出长城、公司改组,名称改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在这件事件上,张善琨的遗孀童月娟和袁仰安的家人各有各的说法:前者认为张善琨是因政治理由,"被扫地出门",后者则将张、袁二人之分道扬镳归咎于"钱银轇轕"4。五十年代于上海出版的《青春电影》半月刊对长城改组的事态发展,一直颇为关注5。据该刊报道,改组后的公司仍由袁仰安出任总经理之职,拉上香港《大公报》的经理费彝民参佐戎机,得到以航运业起家的吕建康全力支持,又罗致司马文森为挑选剧本的顾问,也就是说,打从开始,新长城的左派背景已很清晰。
凤凰的诞生
另一方面,永华既让张善琨这个灵魂人物走掉,经济上又不稳定,其后更因劳资纠纷发生了一次工潮,不少影人不得不另谋出路。这种艰难的处境,再加上那时候追求进步思想的社会气候,便促成了五十年代影业公司的诞生,舒适在本书的访谈中对此便有提及。但它跟大光明、南群、南国等公司有所不同,它不是由老板投资,而是一家合作社式的公司,以员工们的劳动力作为资本。五十年代成立一年,拍了两部出色的影片《火凤凰》(司马文森编剧6,王为一导演,1951)和《神鬼人》(顾而已、白沉、舒适合导,1952),其经营模式和成功经验对后来的"兄弟班"公司如凤凰及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相信也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但一如其他几家带进步思想色彩的小公司,五十年代也没有维持长久,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两、三年里,许多影人北上归国,而留港的不少成员如程步高、刘琼、舒适、李丽华、韩雄飞、胡小峰、白沉、韩非等,也转到改组后的长城和稍后成立的凤凰去了。
凤凰的基本班底多来自龙马影业和五十年代。龙马是由企业家吴性栽投资、费穆主持的一家电影公司。吴性栽虽是商人,但对艺术素感兴趣,对京剧尤其着迷,因其对京剧名角的大力支持而被称为"京剧托勒斯",他对电影的兴趣亦早自一九二四年创办上海百合影片公司开始。他跟费穆非常投缘,曾先后支持他拍摄周信芳主演的京剧戏曲片《斩经堂》(1937),以及梅兰芳主演的彩色戏曲片《生死恨》(1948)。一九四七年,他另组文华影片公司,拍了多部出色的影片,其中包括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他于一九四八年侨居香港,五零年与费穆创办龙马,据韦伟说,吴性栽属龙,费穆属马,故取其名7。费穆于一九五一年心脏病发逝世,吴性栽于翌年退出龙马,内里乾坤恐非我们局外人所能理解。在这个处境中,当时龙马的骨干朱石麟一方面集合原有员工接手管理,一方面筹组凤凰影业公司,并于一九五三年拍了创业作《中秋月》。有别于商人出资的长城,凤凰是一家与人合资组建的"兄弟"公司,并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8。
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影响
要理解所谓"左派电影"在香港电影史上的独特位置,大抵要走进时光隧道,从三十年代的上海说起。
一九三零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发起人有鲁迅、郭沬若、茅盾、郁达夫、沈端先(夏衍)、钱杏邨(阿英)、田汉、郑伯奇、华汉(阳翰笙)、沈叶沉(沈西苓)等五十余人。一二八战争结束后不久,共产党又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领导,不但向当时的电影公司提供具有"进步"内容的剧本,也介绍了许多以"左翼剧盟"为主的新派文艺工作者到各家影片公司去,更在报刊上建立评论阵地,推动左翼电影的创作。在中国电影的整体发展上,左翼思潮的作用是否被高估了,也许可以重新评价,但无可否认,它影响战后的香港电影,则有迹可寻。
打从一九三三年左翼文人参加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他们即在公司内部以编剧委员会的形式,负责电影剧本的创作与修改,五十年代、长城和凤凰等公司都参照了这种集体创作方式。据报道,长城于一九五零年改组后成立了一个编导委员会,由马国亮、岳枫、李萍倩、刘琼、顾而已、陶秦等任委员,讨论剧本内容和演员分配的问题9。从这个名单看来,剧本创作仍掌握在真正电影人的手上,而左派组织的参与还倾向低调,连正牌属于左派系统的司马文森也没有在名单上出现,倒隐没于幕后。新成立的凤凰亦有一个艺术委员会,由朱石麟主持,当时许多电影剧本都是在集体讨论中产生的。曾在长城任编剧的朱克在访谈中说:"在左派公司,编剧的地位很高……有『人民剧作家』之称,回到国内,非常受尊重。"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所谓"九稿十三纲",浪费不少人力物力10。这种集体讨论的方式诚然有优点也有缺点,长城另一编剧查良景在一次口述历史访问中便有相当中肯的说法:好处是经过反覆讨论,作品的质素比较有保证,对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长城、凤凰便培养了不少编导人才;坏处是往往在过程中牺牲了个性,因为艺术讲求创新,而集体讨论却注重集中11。
从编导人才培训这个角度来看,左派公司确有别树一帜的机制,如收入本书访谈中的胡小峰、鲍方、罗君雄等都是内部培训出来的,其他如陈静波、传奇、张铮、张鑫炎等都是从演员甚至剪接出身而晋升为导演的,而作为女性,任意之和朱枫亦获得不少执导的机会,就连贵为第一线女演员的石慧也曾当过副导演,这些做法在其他同期的大公司如邵氏、电懋里便不多见。长城是商人出资,早期集合了岳枫、李萍倩、程步高、黄域等资深上海影人,编导人才比较多,而早期凤凰能独当一面的却只有一个朱石麟,对人才自然更加渴求。凤凰很多出品都挂着朱石麟"总导演"之名,而实际执行的则是联合导演的新人,几部片下来,新人便可自立门户,独立执导演筒了。曾接受访问的影人,从演员到导演,几乎无人不提及朱石麟在这方面的贡献,但从另一角度看,这种眼睛只向内看的做法却又难免封闭。左派公司甚少向外界招揽编导人才,自然也较少受到外间的冲击。这一点跟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界政治立场的壁垒分明不无关系。
影圈左右阵营的关系
中国政权易手后,香港政府对左派的影响力非常敏感,一九五二年初先后两次将十名左派影人驱逐出境12。事过境迁,现居上海的舒适便在访谈中对亲身经历的过程有很幽默的描述。一九五六年,王元龙、胡晋康、张善琨等影人正式成立"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翌年改称"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所有电影若要在台湾发行,拍戏之前都要跟"自由总会"登记,没有他们的证书,台湾方面不会通过,影片便不能在台湾发行。文革前,"长、凤、新"甚至部份中联的出品都可在大陆公映,据五、六十岁以上的国内朋友忆述,当年这些影片都相当卖座,甚至比国产片更受欢迎。这其中双方实际经济上的关系如何,我们局外人不得而知,宜作更深入的研究,但对"长、凤、新"而言,肯定是很重要的支持。然而,这个庞大的市场对"非左派"系统的电影公司却早已关上了大门13。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市场便显得非常重要,除了"长、凤、新"等直属左派系统的影人外,其余大部份人都要参加"自由总会",包括当年的邵氏、电懋/国泰等大公司的工作人员。于是,左派公司即使有心向外界招手,左派系统以外的影人也碍着市场的考虑而不敢加入了;而且,左派公司员工的酬劳也远远不及其他公司。影响所及,"长、凤、新"只好集中力量进行内部的人才培训。
然而,"长、凤、新"倒又不是跟外界绝缘的;事实上,他们跟其他电影公司有很多商业上的联系。五、六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初、中期,邵氏和电懋均未正式开发自己的制片事业,但他们在东南亚却拥有庞大的戏院网络,需要大量影片上映,"长、凤、新"的影片制作严谨,明星有号召力,刚好填补这个空间。那个时候,电懋主要买长城出品,邵氏多买凤凰作品,光艺则买新联的粤语片,各适其所,各取所需。从五、六十年代出品的所谓左派电影看来,中共似乎无意在香港大搞意识形态的活动,只是希望在这个小岛上维系着一个据点,与外界作有限度的沟通。
细看影片的内容,当然部份作品(特别是五十年代早期)反映了战后香港社会的现状及当时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充其量只是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矫饰(如《说谎世界》,1950和《百宝图》,1953),或在片末隐含着返回"乡下"的号召(如《江湖儿女》,1952和《一板之隔》,1952),或委婉地将希望寄托于平民教育的兴办上(如《寸草心》,1953和《姐妹曲》,1954)。更多的作品倒是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与趣味(如《三恋》,1956、《情窦初开》,1958和《眼儿媚》,1958等),在写及现代妇女的处境时(如《我是一个女人》,1955、《新寡》,1956、《寂寞的心》,1956),也总是一方面表现出对个性解放的渴求,另一方面却又不敢太背离保守的社会气候,今天看来,作品往往因而显得有点尴尬。及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香港电影踏入了国语片的旺盛期,邵氏、电懋、长城、凤凰等公司百花齐放,左派电影的题材也越来越多样化,从夏梦主演的上海越剧电影系列(《王老虎抢亲》,1961、《三看御妹刘金定》,1962、《金枝玉叶》,1964)到傅奇、张鑫炎导演的新派武侠片《云海玉弓缘》(1966),从改编文学名著的《故园春梦》(1964)到远赴蒙古拍摄的侠义传奇片《金鹰》(1964),从讽刺喜剧《梁上君子》(1963)到爱情小品《含苞待放》(1966),"长、凤"的路线与毛泽东"廷安讲话"的精神相去甚远。
政治与电影
从另一方面看,经过"长、凤"成立之初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后,国内的政治浪潮似乎开始影响香港左派影圈。袁仰安拍摄改编自鲁迅名著的《阿Q正传》(1958),并没有得到国内的支持,影片尚未正式完成,他便于一九五七年离开长城,另组新新影业公司,《阿Q正传》最后由新新发行14;编剧朱克于本书的访谈中说:"国内大概从一九五四年开始派人来长城。党来了,袁仰安便要走。"这里提及的年份可能不太准确,毕竟已差不多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朱克本人于一九五八年被长城开除,当时国内正进行反右运动,这几件事不知是巧合,抑或反映了国内形势对香港左派影圈的影响。
然而,国内的十年文革,却肯定对香港左派电影事业造成了不能逆转的破坏,这一点,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意见一致。在那天翻地覆的岁月里,有人情绪激昂,裘萍便在一次访问中坦然承认当时参与其事的投入15;石慧、傅奇夫妇亦积极参与当年的"反英抗暴",傅奇是"斗委会"第一批公布的成员之一,夫妇二人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凌晨二时在家里被拘捕,囚禁了一年多才获得释放16。也有人打从开始就不赞成文革,长城大公主夏梦当时刚巧怀孕,便借此不参加左派组织的游行集会,更于一九六七年九月悄然离开香港,远赴加拿大,两年后回港,却从此不与电影界交往,直到十年后才重回电影圈,组青鸟电影公司,监制了《投奔怒海》(许鞍华导演,1982)、《自古英雄出少年》(牟敦芾导演,1983)和《似水流年》(严浩导演,1984)等三部影片。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大抵更多人是心怀疑惑,却又无法置身事外,鲍方便是其一。在本书收录的访谈中,鲍方坦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也拍了一些很"左"的影片,如《沙家浜歼敌记》(1986)和《大学生》(1970),其后便无以为继;一九七四年开拍的《屈原》,直至一九七七年打倒四人帮后才正式上映。之后,"长、凤、新"已不能恢复五、六十年代的元气,一九八二年三家公司合并,组成银都机构,一直到今。
结语
本地人士对香港"左派电影"的研究不多,已发表的文章也较零散。第三届香港国际电影节(1979)的《战后香港电影回顾1946-1968》对战后的进步电影作出了初步的探讨,第七届香港国际电影节(1983)的《战后国、粤语片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更进一步,其中石琪的〈六十年代港产左派电影及其小资产阶级性〉是少数直接讨论左派电影的文章。第九届香港国际电影节(1985)有"李萍倩纪念特辑",对其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作品作出了初步研究。第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1990)的《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有多篇文章探讨香港电影中的中国因素,其中论及香港左派电影的有罗卡的〈传统阴影下的左右分家〉和汤尼‧雷恩的〈转向的拥抱──中共对中国电影的改造及其在香港的回响〉;第十八届香港国际电影节(1994)的《香港──上海:电影双城》论及上海左翼影人在港的发展,并介绍了多部李萍倩在香港时期的作品。一九七八年沈西城编著、翁灵文校订的《香港电影发展史初稿》中有一章写长城的崛起,其中对旧长城到新长城的转折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对袁仰安的角色也有记载17。九十年代中,廖一原、冯凌霄、周落霞、吴邨等合写的〈香港爱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及其影响〉18;陈文、薛后合写的〈香港早期粤语片简述〉19,以及周落霞、冯凌霄、余伦合写的〈"银都"的成立及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20等三篇文章,对香港左派电影的来龙去脉作了较有系统的概括,却对袁仰安这个人物刻意回避。
我们希望这本影人口述历史丛书能引起大家的兴趣,摒除成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出比较有系统的研究。在这里,谨衷心感谢所有接受电影资料馆影人口述历史访问的前辈们,您们的忆述令一段被埋没良久的历史又活了过来,就如同在灰扑扑的底板涂上了丰富的色彩。
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
黄爱玲
2001年9月7日
注释:
- 朱枫、朱岩编著:《朱石麟与电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
- 参看廖一原、冯凌霄(执笔)、周落霞、吴邨:〈香港爱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及其影响〉,收录于蔡洪声、宋家玲、刘桂清合编:《香港电影80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 参看本书〈陆元亮〉一章。
- 参看黄爱玲:〈童月娟:新华岁月〉,郭静宁编:《南来香港》(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1),香港电影资料馆,2000;另参看本书的〈旧影话〉。
- 详见《青春电影》半月刊,上海,1950年3月1日第5期至1950年5月15日第11期。
- 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四卷,香港,次文化堂,2000,21至23页。
- 黄爱玲编:《诗人导演──费穆》,香港电影评论学会,1998,204页。
- 参看廖一原、冯凌霄等前引文章及本书〈韦伟〉一章。
- 《青春电影》半月刊,上海,1950年5月15日,第11期。
- 参看本书〈朱克〉一章。
- 摘自查良景(香港电影资料馆影人口述历史访问),1997年4月1日。
- 1952年1月10日,香港政府入屋拘捕并驱逐了司马文森、刘琼、舒适、齐闻韶、杨华、马国亮、沉寂及狄梵等八名电影工作者出境;五日后,白沉、蒋伟相继被递解出境。
- 早于1950年,中国政府已对电影事业严加管制,是年文教厅文化事业管理处禁映的影片便有八十余部,内有国语片十二部,包括《大凉山恩仇记》、《血染海棠红》、《莫负青春》、《黄天霸》、《一夜皇后》、《国魂》、《两代女性》、《人海妖魔》、《凤还巢》、《奇女子》、《水浒传》、《血溅姐妹花》等,详见《青春电影》半月刊,上海,1950年3月1日,第5期。
- 详见本书沈鉴治之〈旧影话〉。
- 摘自裘萍(香港电影资料馆影人口述历史访问),1998年5月29日。
- 可参考〈新闻专题:六七暴动秘辛〉,《经济日报》,2000年11月28日及
- 沈西城编著、翁灵文校订:〈香港电影发展史初稿〉之四,《新观察》月刊,香港,第七期,1978
- 同注2
- 收录于薛后:《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
- 1996年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在广州召开的"香港电影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